
唐代皇权对司法的影响
——《新唐书·刑法志》读书汇报


《新唐书·刑法志》根据时间顺序撰写,夹叙夹议,不仅介绍了唐代刑书的修订增删、唐代刑罚的演化嬗变,还据其记述的事实,对唐代帝王及其刑罚主张进行了简要的评论,全书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
《新唐书·刑法志》中对于皇帝本人的评论与同时代刑罚的状况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若皇帝“性仁恕”,则同时代的刑罚也呈现出宽平的趋势,若皇帝“性刻深”,则同时代的刑罚会显现出严酷的特征。基于上述发现,我们小组产生了研究皇权与司法关系的兴趣,引发“唐代皇权对司法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1
背景知识
关于皇权。中国很早就产生了皇权的概念,类比洛克《政府论》中对于政治社会起源的阐述,皇权作为一种统治权,最初是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下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缺陷而产生的,因此,古时人们心中皇权的理想状态应当是依靠“受命于天”的“天子”的统治可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一切问题。然而,由于“天子”本人仍然是人,无法实然上达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事无巨细、近乎于神的绝对控制,皇权实质上也就只能作为一种概括性的治权存在。那么,为了使现实的皇权能够不断贴近理想的皇权,构建一个辅助皇权的、行之有效的治理体制迫在眉睫,“礼”和“法”也就应运而生,《新唐书·刑法志》开篇提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作刑书”两种不同的治理手段,正说明了“礼”、“法”之于皇权的工具性。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问题,皇权的治理手段也会随着问题的复杂多样而更新迭代,并生成自身的运行逻辑。到了唐代,作为皇权统治工具之一的“法”,表现出了“轻刑慎罚”、“追求稳定”、“崇尚公平”的特点,《新唐书·刑法志》结尾对于高祖、太宗“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平三代之盛时”的赞誉,充分体现出当时对于“轻刑慎罚”的推崇,“盖法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则表达了刑罚对稳定和社会公信力的要求,而《贞观政要》中太宗反思隋朝“官人百姓造罪不一”的教训,强调“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不私于物”,可见其对于法之公平性的重视。这些“法”所具有的特点,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人们心中,被认为是不应当随意违背的,有效地约束着百姓生活和官员做事,甚至连皇权的实际掌握者——皇帝,亦不能毫无缘由地败法乱纪、肆行不轨。正如《唐律疏议》所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刑罚成为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体制后,于皇权而言的“政教之用”便只是对其进行概括性地治理,不应该也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可以说,在中华大地多如牛毛的案件里,绝大多数是不涉皇权的,但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旦皇权介入司法裁判,便会对司法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探讨这一话题的原因。
关于司法状况。唐代的司法机关总体可以分成中央和地方两级。
唐代的中央司法机关
大理寺
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寺“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设长官正卿和副长官少卿,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

刑部
六部之一,专管刑狱争讼,设长官刑部尚书和副长官刑部侍郎,统领四司

御史台
中央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唐代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副长官为御史中丞。

中央司法机关主要包括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据《唐六典》卷十八大理卿条记载,大理寺“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设长官正卿和副长官少卿,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案件和京师地区徒刑以上案件,正所谓“在京诸司,则徒以上送大理,杖以下当司断之。若金吾纠获,皆送大理”。除审理中央百官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也具有重审权。此外,大理寺还有出使推鞠、管理中央监狱和全国监狱的职能。
刑部为六部之一,专管刑狱争讼,属有四司:刑部、都官、比部、司门。设长官刑部尚书和副长官刑部侍郎,统领四司,《唐六典》中提到尚书、侍郎“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即是说,国家律令刑法、囚徒簿籍、财政勾检、关禁出入等中央或地方政府事务,凡是与刑法、狱讼有关的,都由刑部尚书、侍郎,辨明是非曲直,依据律令格式,予以定案。
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唐代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副长官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管辖国家法制、礼仪、政纪重权。但唐后期,御史大夫成为不常置的官员,御史台的司法监督权也被不断地削弱,至宣宗时,御史台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空间几乎已经被压缩到名存实亡的地步了。
唐代地方司法机关分州、县两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各级地方司法权限有明确规定,对地方司法机构的监督机制也比较健全,从管辖、起诉、立案到审判、监督,都有比较具体的规定。
唐代司法制度虽不如当代那么科学完善,但已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有效的逻辑机制和运行体系,能够一定程度上处理和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和纠纷。当皇权凭借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介入司法时,究竟会对司法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改变?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影响状况分析”中结合案例作进一步探究。
2
影响分析之积极影响
谈及影响,利弊兼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皇权,既是司法秩序的推动者、完善者、监督者,又是司法秩序的损害者和破坏者。我们认为,皇权之于司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完善法律条文。皇帝对案件的审理,能够起到完善法律条文,促进法律发展的作用。
比较典型的案件是《新唐书·刑法志》中所载唐太宗怒杀张蕴古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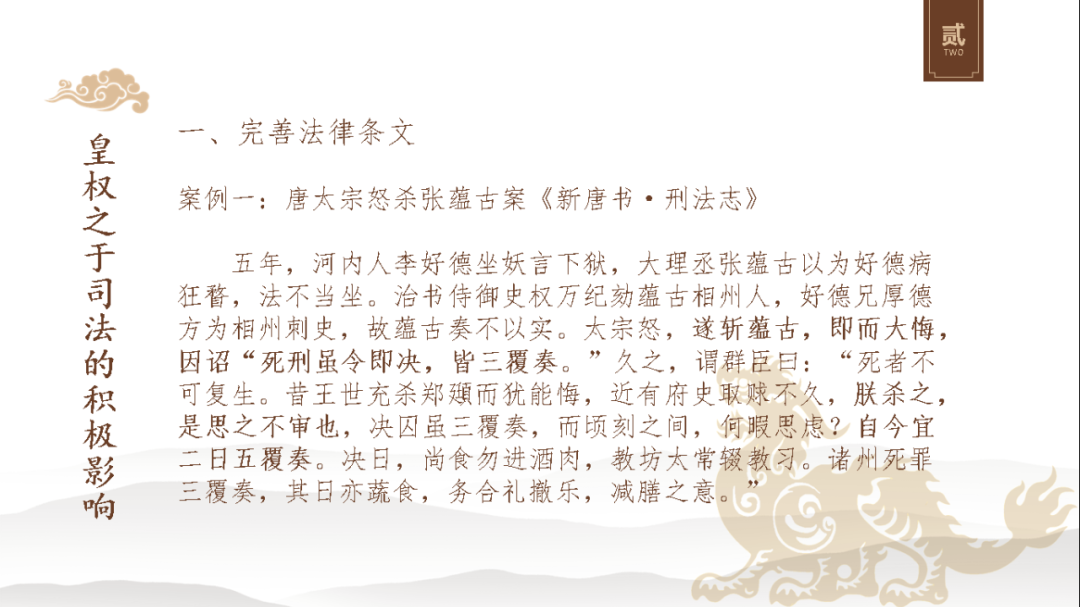
李好德因妖言惑众判罪下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精神错乱,按照法律不应该判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向太宗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又是现任相州刺史,因此他的上奏不真实。太宗听了很生气,马上将张蕴古斩首。但随后又非常后悔,因而下诏:“死刑犯人虽然下令立时处决,但也要三次禀复奏报。”过了一段时间,又对官员们说:“人死不能复生。处决死囚虽然三次奏报却依旧是在顷刻之间,哪有什么思虑的余地?自今以后,应该二日之内五次复奏。”
唐太宗虽然因一时生气怒杀了张蕴古,但其经过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后,认识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创造出的三覆奏和五覆奏制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冤假错案的纠正,也完成了唐代死刑复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张蕴古虽死于唐太宗的盛怒,但也正是基于错杀张蕴古的悔恨中,唐太宗从中吸取教训,要慎罚恤刑,避免滥杀无辜。唐太宗虽并不是死刑复奏制度的首倡者,但他对死刑复奏制度的完善贡献很大,健全完善了唐代的法律制度。
同样被记录在《新唐书·刑法志》中的房强兄弟案,也产生了完善法律的效果:

旧时法律规定,兄弟分居,互不蒙荫得官,但牵连坐罪,却都是死刑。同州人房强因遭弟弟谋反牵连而判死刑,太宗录囚时,对其十分怜悯,提到:“谋反和谋大逆有两种情况:一是兴师动众,二是恶言犯法。轻重本来不同,却同样叫做造反,牵连处罪都判死刑,难道是确定不变的法律?”房玄龄回应道:“按照礼制,孙辈是祖辈的受祭人,所以有孙子蒙受祖父功勋而得官的法令,这说明祖孙血亲重而兄弟血亲轻。”于是法律修改为:谋反和谋大逆罪的犯人,其祖孙和兄弟因牵连而处罪,一律配交官府为奴:但恶语犯法的犯人,其兄弟只处流放而已。
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房强会因连坐而被判处死刑,然而正因为唐太宗对司法的介入,看到了现有法律的不合理处,从而纠正了法律的错漏出,修缮了法律,使法律更趋于合理。并且进一步的完善了法律条文,使整个司法体系更加完整。
从张蕴古案、房强兄弟案中,我们可以看出,皇权的干涉固然是司法体系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但统治者对个案的审理,也能成为激发司法体系改变、创新的一个起点。因此皇权干涉司法是能够起到完善法律条文和法律体系的作用的。
第二,贯彻立法思想。“轻刑慎罚”作为唐代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深刻影响着唐代司法,不可否认,唐代立法中已经尽力做到了“轻刑慎罚”的要求,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总是多种多样的,司法官员囿于法律条文,在实际执法中很难真正去深入贯彻这一原则,而皇权介入司法,恰恰能够很好地实现最初“轻刑慎罚”的立法目的。具体来说,在皇帝干预司法的案件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案件——复仇案。儒家孝义文化认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也就是说,当时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鼓励复仇的,但是唐代法律体系中对于杀人的规定已十分完备,杀人行为因严重侵犯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而被严厉禁止,这也就导致了礼与法之间的矛盾。面对复仇案,普通官员明知情有可原,却依旧无法“轻刑慎罚”,此时,皇帝对司法的干预往往能有效化解这一问题。皇帝能够利用皇权对具有复仇性质的案件进行一种特赦,从而起到减轻刑罚的效果。
例如《旧唐书》中的康买得救父杀人案:

康宪曾借钱给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可是张莅借了钱之后久久不肯归还。于是康宪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康买得上门讨债。没想到张莅刚喝了酒,不但不肯还钱还与康宪发生挣扎,厮打在一起。张莅趁酒劲将康宪咽喉扼住,眼看康宪就要窒息。站在旁边的康买得见张莅力气大,而父亲的情况又十分危险,于是他就拿起一把铁锹猛击张莅的头部。张莅的头被铁锹重击后流血不止,父亲康宪因此得救,但是张莅却因为伤重,三天后不治身亡了。根据律法,康买得应当判处死刑,但皇帝认为他“为父可哀”,如果刻板地遵从法律,“恐失原情之义”,最终为康买得“减死罪一等”。
无独有偶,在富平县梁悦为父报仇案中,梁悦为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果后到衙门请罪,皇帝也下令减死一等,甚至还引发了韩愈等人对于是否要将复仇之法列入法律中的讨论。
梁悦、康买得都因自己的孝义行为得到了皇帝的特殊赦免,唐代立法者基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儒家思想,结合在当时社会业已形成的法律观念,就司法实践中的复仇问题及立法中亲情与法律的冲突问题,引礼入律,为法律确立了一条解决礼与法,情与法冲突的模式,也进一步贯彻落实了“轻刑慎罚”的立法原则,使唐律的刑罚体系获得“宽简适中,得古今之平“的美誉。
第三,监督法律实施。因皇帝具有概括的治权,司法权必然是皇帝行使权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皇帝并不参与日常的司法工作,其对司法权的掌控往往通过录囚制度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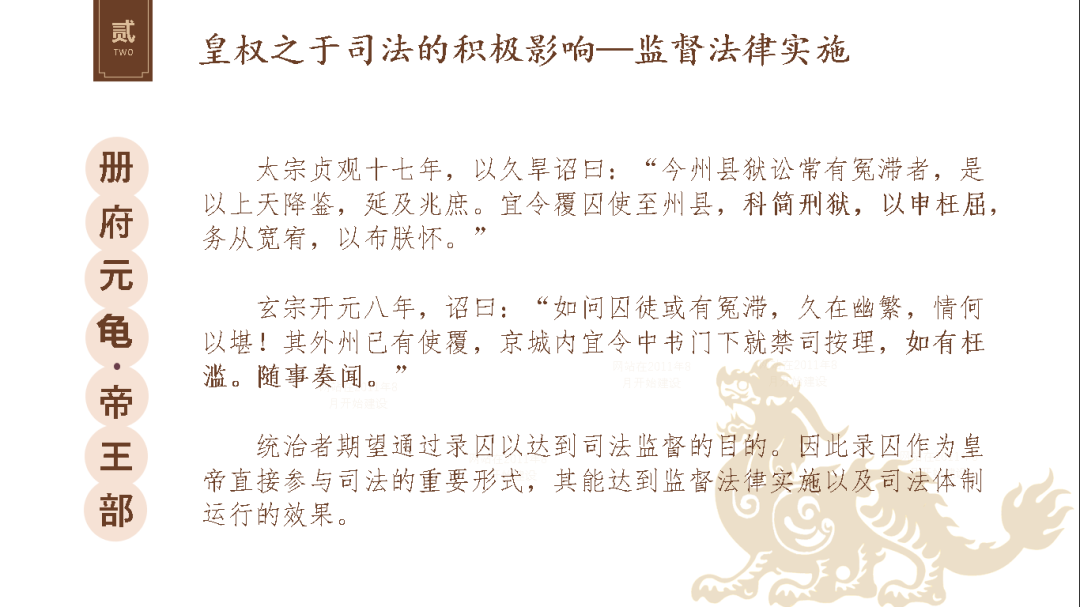
在唐朝时期,由于受到灾异天谴论的影响,每当出现灾害或异象时,经常会通过录囚这一形式来彰显君主的仁善,期望通过录囚来消除灾祸,作为一种仁政其结果往往能达到减轻刑罚的效果。玄宗时期就有因“日食”、“炎旱”、“连雨”等现象录囚的情况。而德宗、宪宗时期录囚的原因是“久旱”,穆宗时期录囚原因有“改元”、“疾愈”等。可以看出,唐代皇帝录囚的时间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也就达到了中央通过对案件不定时地再次审理,有效监督司法的目的。
此外,通过陈玺在《唐代诉讼制度研究》司法监督制度部分的表格节选可以看出,在唐代,录囚的范围不仅包括京畿囚徒,还包括益州道,夔州,关内诸州,广州,甘州,崖州等各个地方,录囚范围极广,基本覆盖全国各地,皇帝以此保证对全国司法的控制,同时也起到了对各地的司法运行进行监督的作用。在《册府元龟·帝王部》中记载,太宗贞观十七年,以久旱诏曰:“今州县狱讼常有冤滞者,是以上天降鉴,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县,科简刑狱,以申枉屈,务从宽宥,以布朕怀”;玄宗开元八年,诏曰:“如问囚徒或有冤滞,久在幽繁,情何以堪!其外州已有使覆,京城内宜令中书门下就禁司按理,如有枉滥。随事奏闻。”从唐太宗、唐玄宗的诏令中,都可以看出统治者期望通过录囚以达到司法监督的目的。因此录囚作为皇帝直接参与司法的重要形式,其能达到监督法律实施以及司法体制运行的效果。
3
影响分析之消极影响
皇权借由自身超然的权威,固然能够在某些问题上促进司法,但皇权干涉司法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费孝通、吴晗等人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也指出“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都有意无意的把皇帝的真面目神圣化和凡人不同,在老百姓心里皇帝是天生的圣人,可望不可及”,然而,“即使皇帝是处在法律之外的一个位置,如果皇帝的权利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那国家司法机构必然会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因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皇权突破法律给司法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一,皇权干涉司法会导致法律的公信力不断降低。“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司法秩序需要严格遵守、反复践行才能树立起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和信仰。皇权却常常以极为强势的态度干扰司法,贞观初年甚至出现了“太宗务止奸吏,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上怒,将杀之”的钓鱼执法行为。正是皇权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影响司法,才导致皇权在改变司法审判结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法律的混乱失序和人民之于法律信任感的降低。

以刚才提到的“张蕴古案”为例,太宗认为张蕴古失出,盛怒之下将其杀死,而按照唐律,“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显然,唐太宗的判决违背了唐朝律法,而随意突破法律的后果便是“今失入无辜,而失出为大罪,故吏皆深文”,官吏们宁可犯“减三等的失入罪”,也一定要避免“减五等的失出罪”,只是因为唐太宗缺乏深思熟虑的一个决定,人们便不再相信唐律中对于失出之罪减五等的规定,以至于此条规定几至成为一纸空文,可见皇权干预司法对于法律稳定性和公信力的损害之大。
唐代杜佑所撰写的《通典·刑罚七》中记载的权善才、范怀义昭陵斫柏案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公信力破坏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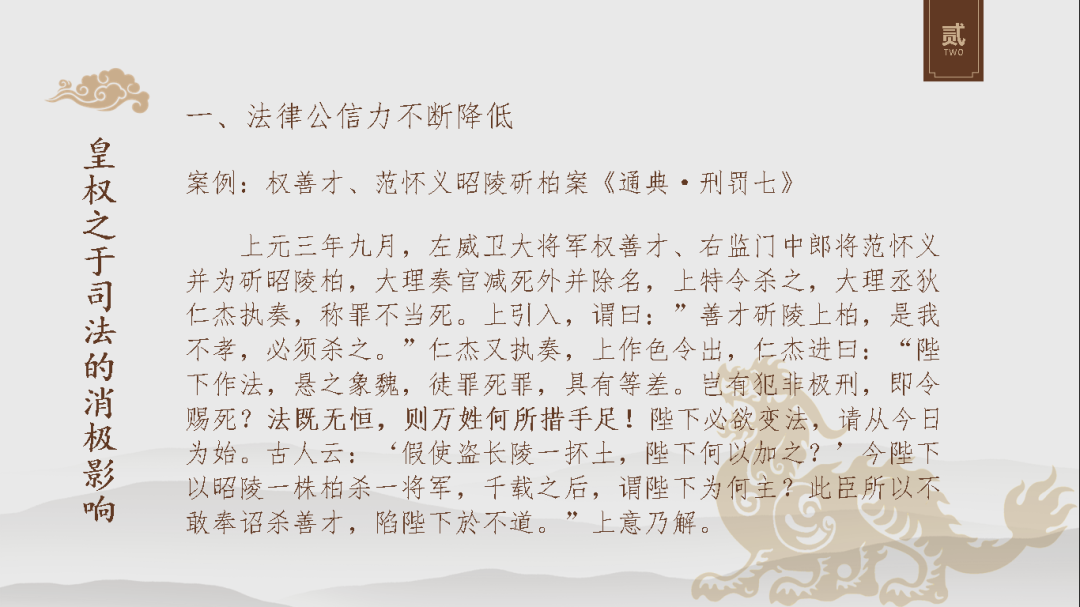
唐高宗上元三年九月,权善才、范怀义一起在昭陵砍柏树,大理奏官减免了他们的死刑,但开除了他们的官籍,但高宗下令杀死两人,大理丞狄仁杰坚持认为他们罪不至死,于是向皇上进言,陈述了皇权任意干涉司法的弊端:“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恒,则万姓何所措手足!”法律如果不能保持稳定,朝令夕改,令出弗行,那天下的百姓就无法依据法律来判断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也就不会再相信和遵守法律。
司法制度秩序分明、结构清晰,官吏严格依法办事、依律量刑,才能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皇权置于法上却不能保持足够的谦抑性,频繁主动的干涉司法,即使在“权高于法”是社会共识的时代,对法律公信力的破坏力仍旧是巨大的。
其二,皇权干涉司法会强化阶级不平等和司法特权。中国古代社会是“父权家长制”下的社会,皇权则是父权在观念上的延伸,所谓“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天子受命于天,皇权至高无上,有着与生俱来的身份特权和等级秩序,当皇权介入司法,审判结果也就不知不觉地强化着等级特权。《贞观政要》记载的长孙无忌带刀案中唐太宗对于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反映出这一问题: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皇帝召见,没有解下佩刀进入了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发觉,罪应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内,应处做苦役二年,罚铜二十斤。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校尉没有发觉,长孙无忌带刀入内,同是错误罢了。臣子对于皇帝,不能称作错误,依据法律说:‘供皇帝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合法律的,都处死。’陛下如果记取长孙无忌的功劳,就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判决的;如果应当根据法令,罚铜不是合理的。”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便要枉法呢?”再命令议论定罪。封德彝如当初一样坚持定议,太宗又想听从他的定议,戴胄再次反驳上奏说:“校尉因为长孙无忌而获罪,在法律上应当从轻,如果给他们的过失错误定罪,那么作为情节是一样的,可是生死立刻不同,因此我坚决请求考虑。”最终太宗免除了监门校尉的死罪。
同样是犯错,唐太宗对待带刀入内的长孙无忌百般回护,对于监管不力的监门校尉态度却截然相反,即使太宗表面上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合议后却还是“将从封德彝议”,即使最终在戴胄的劝说下免去了监门校尉的死罪,却依旧没有回应戴胄提出的对长孙无忌量刑畸轻的问题,对长孙无忌持有明显的庇护态度,使得等级特权在司法中进一步被强化。

《新唐书·刑法志》中的广州都督瓽仁弘贪赃案也同样反映出这个问题。太宗明知自己“宽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负天”,却宁愿“令有司设藁席于南郊三日”请罪,也一定要违背法律将“法当死”的罪名“贷为庶人”,不仅仅因为瓽仁弘“老且有功”,也因为他“助高祖起,封长沙郡公”,身份地位不同于常人。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当司法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时,皇帝作为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代表,必然会以行使皇权的方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强化司法中的阶级不平等和等级特权。
4
成果总结
张星久在《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一文中指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也就是说,皇权本身就存在皇帝个人能力与皇权权力性质不对称的矛盾,结合我们对于皇权影响司法状况的研究,我们认为:皇权对于司法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积极促进的一面,也有消极破坏的一面,但整体来看,积极影响更多受到皇权背后的掌控者即皇帝个人性格等情况的左右;消极影响则更多直接根源于皇权本身所具有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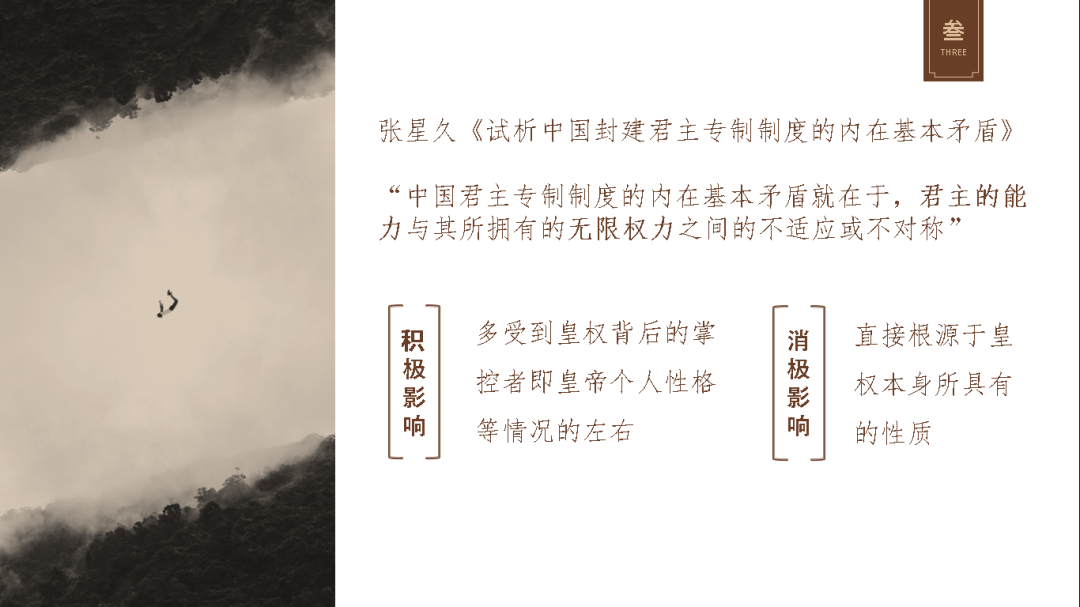
据此,我们总结了以下结论:
第一,唐代的司法状况与皇权的掌控者(即皇帝)有着不可忽视上的联系。皇权作为一种无限权力,其本身是否能够受到节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性格和能力,取决于皇帝是否愿意听取意见。纵观《新唐书·刑法志》,均是以皇帝个人性格和能力的评述作为引入,介绍其在位期间的法律状况。唐太宗时期,张蕴古案能够实现唐代死刑覆奏制度的完善,能够及时消除失入失出不如法的弊端,十分依赖于太宗本人对刑罚的审慎态度,正是因为太宗能够严格遵从司法流程断案,尽量听取专业司法官员的意见,错案出现后也能够及时反思纠正,贞观时期的司法状况才能得到后世的赞扬和推崇。相反,武则天在位期间,因武后生性多疑、偏爱酷吏,便修告密之法、大兴刑狱,以至于司法官员以用法苛刻为功,多为后世所诟病。安史之乱后,喜刑名的肃宗“伪官背军归来,胁从者相率待罪阙下,斩于独柳树下者十一人,赐自尽于狱中者七人,决重杖死者二十一人”,而同样处于混乱之中的代宗却因性仁恕而下令“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前后相差不过几年,司法状况却大相径庭,可见“非事异也,盖人不同耳”。
现代社会虽然不存在如皇权一般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归根到底依旧需要人来实施,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人性格和能力的影响。彭宇案中,法官不当地运用了生活经验推理却没有给出合理的适用理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司法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坚持依据法律规定,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和生活经验,独立对案件进行判断,并严格遵从自由心证的要求,公开判断理由和结果,接受当事人和公众的监督。
第二,唐代皇权对司法的影响可以为现代的制度建设和程序完善提供借鉴。封建社会中的皇权拥有绝对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依旧能够借由司法制度和程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制约,现代社会的司法就更加应当充分发挥制度和程序的作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唐代的张蕴古案、卢祖尚案之于死刑覆奏制度,现代的张氏叔侄案、杜培武案之于被告人权利保障制度,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当不断规范非法证据排除、审判监督等重要程序和制度,2020年两高三部联合印发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通过拓展值班律师制度的覆盖面,强化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刚性力,规定检察机关的说理机制,以实现对人权的充分保障,就是程序和制度有效预防冤假错案的证明。
阅读《新唐书·刑法志》,我们常常会疑惑,为什么《新唐书·刑法志》作为一本史书,相比于《旧唐书·刑法志》,对于史实的记载竟如此简略,甚至有些粗糙,却把大量笔墨放在了阐述看法和观点上。随着我们思考的深入,我们才意识到,《新唐书·刑法志》作为一本宋人为唐代修的史书,比起编撰《旧唐书·刑法志》的唐人,其心态或与现在阅读《新唐书·刑法志》的我们更加相似,都秉持着“以史为鉴”的态度,通过评价皇帝性格、法律,试图总结法律发展的规律,堪破王朝兴替的奥秘。只不过千年前的他们,期待一个贤明的君主再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而千年后的我们,相信更加完善的制度和程序才是真正能够保障法律前行的力量。